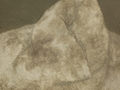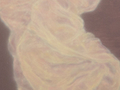岳海喜并没有描画死去的当代人。在画家笔下, 那些只是在一瞬间失去神志、处于无欲无求的真空状态的“人形”而已。这些“人形”失去了生命的力量,也许正在做休息和补充;也许只是切断了和外界的一切社会学意义关联,将自己还原成一个碳水化合物的生命体—不管如何,他们暂时和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无关,他们只是某一时间、某一个特定房间里的无意识的存在。这种存在目前来看,只有美学意义。
画面纯灰的色调加强了这一艾略特式的意象。画家娴熟、令人惊讶地运用微妙的银灰色调,在色彩的冷暖微差之间,小心翼翼地营造出一个私密的感性空间,一个有着张力、质感但同时本质是空无的空间。苍白的光线和光线之外留下的暧昧的阴影加强了生命的无力感,画面被绝望、沉思和巨大的空无感所萦绕。
作为一个年青艺术家,为何他所营造的情景如此沉重,却又如此完整?说好的青春期荷尔蒙冲动呢?说好的对富裕时代的泼皮调侃呢?
1903 年冬天的巴黎,寒气逼人。毕加索连取暖的钱都没有。为了抵御夜间的寒冷,毕加索不得不烧画取暖。熊熊的火焰吞噬了毕加索的素描和水彩画,也吞噬了毕加索的自信。他曾怀疑自己作品的价值,怀疑自己所走的道路。这期间毕加索的创作被称为“蓝色时期”,是他第一次形成自己风格的时期。
大凡上天眷顾的艺术家,上天必定会给他一段困窘的时光,让他一无所有, 让他在世俗的万般羞辱之中不得不转向自己的内心寻求依靠。他寻到的东西,则必是日后成名之时所向披靡的东西。毕加索在他的“蓝色时期”,避开光感和深度的感觉,把人物结合成一种简单的图样,其中沉重、强烈而流动的线条,给人以不真实的、虚拟世界的印象。这种线条具有情感的重量,画家后来的作品大多具有这种富于表现力的线条的特点。这些特点是从观察人的动作和姿势中得到的。那时候的蓝色,是贫穷和世纪末的象征,作品多表现一些贫困窘迫的下层人物, 画中的人物形象消瘦而孤独。
我并不熟悉岳海喜的生活,但也依稀猜得出大概:给人带来巨大折磨的美术学院入学考试、昂贵的学习生活费用和边学习边谋生的经历、美院老师的苦口婆心和对艺术前途的痛苦和迷惘⋯⋯这些构成了中国的美术学院几代学生共同的人生体验。所不同的,是属于岳海喜这代年青85 后艺术家特有的外部环境。
他们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年的最高潮时期成长,见证了繁华、暴富和神话,也见证了欲望、沉沦和悲剧。依托互联网,他们知道的太多,也懂得的太多。没有上一代80 后艺术家在富裕年代对社会的调侃、对艺术的精明算计;在他们敏感的直觉中,他们知道这一切行将结束,财富消散、名望陨落,所有曾经获得的, 终将还回去。于是他们不愿多说,也不愿多做,他们只想做回自己——一如艾略特意象中“水里的死亡”,在与己全无关联的欲望之海中,静静沉思。
难得的是岳海喜的沉思是如此的彻底,如此的孤绝。恰如毕加索的“蓝色时期”一样,关注心象的艺术家大多采用压缩色域、压缩画面空间感的办法,来取得纯粹感;将衣物服饰删减到最少,甚至索性裸着,也是艺术家的通常做法。惟其如此,才能直面赤裸的人性。与100 年前的毕加索不同的是,在今天的少年笔下,人物不再是内省而孤独——他们被散去了理性,甚至被散去了自我,成为一具无目的的躯壳。雅克·拉康(Jacques Lacan,1901 – 1981)认为,“自我”是通过镜子和他人的确认而建立的,如今在岳海喜的笔下,这些“人”放弃了身份和自我,回到一个分裂、混沌的状态,回到一个无我、无它的心象。
我们不妨将岳海喜画面中的意象看做新一代艺术家无声的艺术宣言:他们用“空无”来对抗这世界的“欲望”—世界不再是你们的,也不再是我们的,世界已经分裂成无数个无意义的碎片,我们每个人在享用的同时,“人”已不在。
2014 年大暑前于小谷围
(吴杨波 中央美术学院国家艺术发展战略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在读博士,广东省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委员,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,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学术委员,《南方艺术》执行主编)
![]()